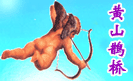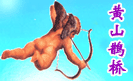1980年——1985年间,全国各地曾兴办了不少的婚姻介绍所,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继夭折。2000年以后,婚姻介绍所再度在全国兴办,可伴随着虚假广告、乱收费、雇佣婚托、提供色情中介服务等许多新问题的出现,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批评。事实上,面对婚姻这一终身大事,人们大都希望有个能方便男女相互选择的信息中心和社交平台。故此,成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汇集适当区域各个层次的寻偶男女,通过基本情况登记和提供相关服务,扩大当事人的择偶范围,这本是一件顺应社会需求、成人良缘之美的大好事情。然而,这种中介机构——婚姻介绍所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实践过程,却一直是收效微微。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工作方法不科学。回顾1980—1985年间,各地或匆忙组织大男大女开展集体交友活动,或快速成立婚姻介绍所专门服务,尽管这大都出自好意,但却忽略了当事人的择偶保密心理和相关要求,并对社会上复杂多变的人与事缺少审慎地考虑和相应的对策。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上海、温州、成都、通州等地推行的签定《婚姻介绍服务合同》办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由婚姻介绍所事先拟定的这种格式契约的作用,实际上只为婚姻介绍所的反复收费提供保障,但对付出不少钱财的寻偶人来讲,既不能得到服务成功的保证,更不能得到服务不成功的赔偿。例如合同中的“按规定标准支付登记费、服务费及自愿支付其他费用(如约见费、茶水费、活动费等)”条款,所谓的“规定标准”,乃婚姻介绍所一方说了算数;所谓的“自愿支付”,系寻偶人一方不得不承担的一次次重复交费。又如寻偶人“登记结婚后,须在一周内书面通知乙方(指婚姻介绍所),未通知者自行承担相关民事法律责任”条款,其实暗藏着婚姻介绍酬谢金、结婚红包、新郎喜钱、新娘喜钱等收费项目,这显然是假以履行合同条款名义,实为“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说法和提法不恰当。婚姻,指结婚的事;因结婚而产生的夫妻关系。婚姻,有个男女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相识——是在两人不认识的情况下,通过他人介绍、帮助所发挥的作用,这很重要,但过程很短。而相知和相爱,则是当事人之间的一段较长时间的交往。其最终结合为夫妻的决定,也是当事人自己拿的主意。按照“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应予认定:凡是通过他人包办缔结的婚姻和通过人贩子买卖缔结的婚姻,属于介绍婚姻。而凡是当事人自己拿主意缔结的婚姻,属于自由婚姻。所以,当今流行的“介绍婚姻”说法和“婚姻介绍所”提法是不恰当的。
有人说,“介绍婚姻”这一说法和婚姻介绍所提法,可以当作“约定俗成”看待。笔者认为,将这种回避规范随意性强的解释,套用在“择偶”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上,危害甚大:一是概念不明确,必然造成人们思维和判断上的混乱;二是形式不规范,已经对内容产生反作用;三是名不正言不顺,正面宣传工作难开展。
更须强调的是,“介绍婚姻”(婚姻介绍)这一概念的含义和本质属性——由他人拿主意,使男女发生婚姻关系——这原本是包办、买卖和诈骗婚姻的操作过程和共同特征,是一种婚姻缔结方式(或称确定婚姻关系途径),是几千年来旧的婚姻制度和旧习俗的集中反映。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介绍婚姻”这一过时用词乱加外延,既违背法理又远远落后于实际情况和时代要求。而早在1984年底,巴金先生就曾批评指出:“婚姻介绍所是历史的倒退,包办婚姻的复活。”此言至今还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连续当红娘26年,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专业红娘工作,应当定性为“择偶服务。”具体地说,主要是信息服务职能加社交中心职能,同时兼有婚恋问题咨询职能和相关法律知识与科学知识宣传职能。基于上述服务性质和范围,各地的专业红娘机构,定名“ⅹⅹ鹊桥中心”为好。因为该名称用词恰当无歧义,既寓意成人之美,又包含相关功能。
实践还使笔者认识到,鉴于婚姻介绍所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和重要性,政府相关部门要尽快地对它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顿:一是从理论上明确是非,扶正驱邪;二是出台相关的行政监管办法,工作到位;三是各地的该类中介机构都应公布详细具体的规章制度和公平合理的服务收费项目与标准,做到手续简便、操作严谨、方法多样、服务公平、公开(在一定范围内),同时注意防范登记人中出现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行为,从而使得这项工作朝着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江利刚 / 撰写于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