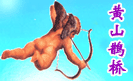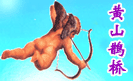与妻相识, 得益于她一同事带我去她家一趟的“走走”。因事先没有“媒妁之言”,故她对我一无所知,而我却是目的明确有意造访,还事先设想了继续接触她的方式方法。可到她家说说话儿之后,我原本想好了的制造事由借两本书回家看看,却临阵心慌犹犹豫地不好意思开口。倒是她见我持书不放有意借阅,便落落大方地说道:“要看,你就拿去看呗。”从此,我以借书、还书为名,一次次迈进她家门坎,也一步步走近她的心坎。
说来我属胆子大的。她是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女儿,而我只是一名职工子弟普通工人,竟敢闯进当年那颇有些威严和名气的县委大院“书记楼”里她的家。也算是我福气好和机遇巧吧——乡村长大心灵纯洁的她本无某些干部子女的娇气和傲气,在屯溪短暂读书又下乡插队更增强了她善良与勤劳的品格,之后被招工分配到县仪表厂装配车间来工作,或许是其“部长女儿”身份的缘故吧,一时竟没有小伙子敢去接近她这位朴素诚实的姑娘,倒让我充当不速之客乘机拣了个大大的便宜。
记得我邀她第一次走进我家那多人共同生活的小平房时,她毫不嫌弃还带满意样地对我说:“没想到你家还有自己的房子。”记得我俩结婚时,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里,就一张写字台、一个中衣柜和一张架子床,她也高高兴兴。特别是她爸爸提出的婚事简办要求——头一天她来我家,第二天在我家举行婚宴,第三在她娘家办1桌宴席,全过程不搞接亲、送嫁仪式,对此她毫不计较同样高高兴兴。再说我俩结婚的这头一天——1982年9月30日,我一大早骑个自行车去她家,用一根布带子捆上她的两条新被子往肩膀上一扛,单手骑车一溜烟地搬来家后还去工厂上班,接着才是我的两个弟弟先后去那儿帮助拿上脸盆、热水瓶等,如同走亲戚般一起徒步走来渔梁我家。且不说这一整天她是杀鸡拣菜洗洗涮涮帮我妈妈准备第二天的婚宴,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该说说那天晚上的经历——因为我要参加县曙声业余团的国庆演出和演出完毕的卸台事宜,而她则只能一个人看完演出后还迟迟等不到我这新郎官而强忍委曲默默无言地回到娘家……
记得我俩结婚后的好多年,她几乎都是在我业余时间不着家的日子里渡过的。先是我要继续参加县曙声业余乐团的学习、排练和管理,紧接着是参加职工夜校初、高中学习,随后又投入到漫长的创办鹊桥中心——与单身男女频繁交往的连续活动之中。对此,她从来没有拉过我的后腿,而只是经常地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借小孩之口说声“早点回家”,送我出行;再准备好热茶热水等至深夜,候我回返。参加曙声业余乐团活动期间,我时常在晚上下课后要送女团员回家,她从来都不计较。搭鹊桥过程中,有时候我要带女同志前往约定地点相会,人家看见了告诉她,她知道后最多也只是笑嘻嘻地问一句“你某日某时到哪去啦”,再不深究我的行踪。
记得我俩跟我父母共同生活10年整,由于是我母亲管家,而我母亲过日子特别地能节省,表现在日常的伙食安排上就是天天见素菜,难得有荤腥,还时常地弄个菜饭、菜粥什么的糊弄一顿,尽管这曾让我妻子她在暗地里多次流过眼泪,但她却从未因此跟我母亲红过一次脸膛。
再说自从我俩独立生活起,买菜烧饭洗衣搞卫生等家务活儿都是她一人包干,小菜园里下种栽苗锄草施肥也是她竭力包揽,同时她在工厂里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好,还常常加班加点多做超产奖金,装车卸货赚点劳务费等,总之是竭尽全力地给家庭多增加点收入和多节省点开支,并且全力支持我的鹊桥事业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难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1年夏天,那正是我和她的热恋季节,我安排一对大龄青年在电影院里初次会面时,出于保密措施上的考虑,就叫她陪姑娘我陪小伙子分坐于当事人两旁。对此她不仅没意见,还主动地在电影院里递瓜子传悄悄话儿给人家,而我这唱“红娘”主角的则落了个清闲自在。再说她跟我结婚之后,曾陆续把所在工厂的大龄姑娘和小伙子一个个介绍给我,先后一道儿促成了6个人的美满姻缘。还有我这鹊桥中心登记的男女,她不仅帮助接来送往,有时还招待他们吃饭,甚至陪远道而来的女客渡过夜晚……
往事悠悠,历历在目,写下此文,夸奖我妻——汪丽珍也。
江利刚 / 撰写于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