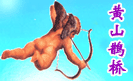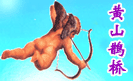2004年6月某日,一名姓方的中年男子,受墙头广告的引导,走进歙县某服务中心,想找一对象。不料,他先后两次受到中介与婚托的联手哄骗。
方某原是上海知青,曾在宁国港口煤矿工作,因长期从事井下作业,加之自己性格内向的缘故,年近半百,尚未娶妻。两年前,单位改制,他下岗失业后,将成家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考虑到凭自己的条件回上海去找对象难度太大,便转念来到外婆家所在地——歙县,先在县城向阳路买下了两室一厅的二手房,装潢一新置办了家具等,这才开始找对象。
在歙县某服务中心那密密麻麻的征婚信息栏内,方某看中一年龄37岁的丧偶女子情况。应服务中心要求,他相继交上了表格费、介绍费之后,这才得知信息栏内所指女子名叫张桂花,同时被安排与对方的哥哥先会个面。对方哥哥跟他约定:第二天上午8时在河西公园男女面谈。
话说张桂花,与方某相识不过个把小时,要了见面礼360元后,就表态愿意跟他结婚,并且将大喜的日子定在10月1日。于是,应张桂花的心愿,方某陪她上屯溪“逛街”。接连3天,不算吃喝和路费,光是在超市里拿这拿那所花的钱,就有800多元。中途,张桂花还带方某去岩寺一居民区坐过一会儿,说那是她小姨家。但是,3天过后,原本笑咪咪的张桂花突然中断联系。一周过后,不知对方住址和电话号码的方某,不得不去服务中心打听消息。
不料,服务中心老板告诉方某:“你这个事情,都是对方哥哥联系的。他在歙县公安局工作。他已来过,说是再也不管妹妹的这闲事了,并且把档案撤走了,因此,我也不好跟他联系了。再说,前两天,恰好有个跟你的遭遇差不多的男子来我这里,说他花掉1000多元钱,结果不成功,也就算了。这样吧,改天有机会,我再帮你找一个。”
生性憨厚的方某被中心老板的一番话弄得晕头转向,想想自己既不方便向服务中心追究责任,又没有勇气去公安局找那不知姓名的哥哥讨回损失,无奈之下,就把自己那寄托成家希望的新房子给卖了。
卖掉房子准备回到父母身边去的方某,一方面难以排除心底那份吃亏过后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对中介机构的能力又还抱有一丝幻想,故临行之前,再次走进歙县某服务中心,然而,他险些又一次掉进婚托的陷阱。
服务中心老板这次一看见方某,就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方同志,你来得正巧,我刚刚为你跟门口的这位女子联系过了。她叫李翠娥,今年29岁,跟你一样是下岗职工。她妈妈在我们这儿的县织布厂工作……”
“不合适吧,我都快50岁的人了,而她还不到30岁啊。”方某想了想道。
“不要紧,我愿意。”门口的李翠娥主动地搭话了。
既然人家愿意,自己不免动心,两人一块儿去饭馆“座谈”。临分手时,李翠娥提出结婚条件——在城里买套房子。
“我已经买过房子,但又卖掉了,钱也寄到上海去了。不过,我有两个舅舅住在本城里,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若急用钱的话,我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借。”
“那也行。不过,钱借来后,要是存银行或者买房子,可一定要用我的名字噢。”李翠娥直言不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心怀疑虑的方某,赶紧找人咨询。一位曾经跟他外婆共同居住一老房子的退休干部吴同志告诉他:“明天你跟她会面时,问问清楚她妈妈叫什么名字,在织布厂哪个车间上班。然后,我再去给你了解了解。”结果,李翠娥察觉到对方有了防备,说了句:“你对我不放心,拉倒吧。”拔腿就开溜了。
警惕啊!着急找对象的人们。
江利刚 / 发表于《黄山日报》2005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