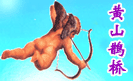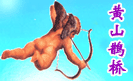| 正如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总有看不见的细菌滋生一样,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的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偏远而贫困的山村里,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 几天之前,本报短信平台上一条神秘的短信,揭开了隐藏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小弄乡鲜为人知的“婚骗”迷局。短信的主人杨洪昨日到昆明市晋宁县公安局晋城分局投案自首,因为此前他回到家乡参与了一起“婚骗”行动,将村中的一名妇女带到河北承德,“卖”给了一户农民。此后,连日做噩梦的杨洪良心发现,在公安局做完笔录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得到了心灵的解脱。 杨洪是解脱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从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走出来,看见了光明。”但是,他的家乡却远没有因此走出“婚骗”的阴影。 有关“云南媳妇”的新闻已多次见诸报端,山东、河北、陕西、广东等地的贫困地区均出现了她们的身影,而且所有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模式:贫困山区的汉子花钱买妻,而后看似贤惠的“云南媳妇”在十天半月或几个月后不翼而飞。这些“云南媳妇”不仅仅来自杨洪的家乡麻栗坡县,还有瑞丽、盈江、宁蒗等地——婚骗,在云南的贫困山区,已经成为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在杨洪的家乡,麻栗坡县小弄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包括杨洪许多亲属在内的大部分村民都参与了“婚骗”。或者说,将村中的女子“嫁”到外地,已成为村民的一种谋生方式。当然,这些“嫁”出去的女子一段时间之后会回到村中,正如当地一种形象的说法——放鸽子,而家养的鸽子总会飞回来的。在“鸽子飞翔”的过程中,“鸽子”本人或其家人将因此获得一笔介绍费,尽管更多的钱被中间人非法牟取。无疑,这是一种诈骗行为,但可悲的是,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在当地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并为大多数村民所认可并效仿。 在整个婚骗过程中,法律意义上的受害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最终被骗的“买妻”者,而其他所有人——包括中间人、“鸽子”、甚至包括“鸽子”的父母亲属,都参与了婚骗行为,都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如果除开从中渔利的中间人,我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人都是受害者:被“卖”的女子多有丈夫儿女,她们背井离乡远“嫁”外地,其辛酸可想而知;那些为了几百元钱就将女儿或妻子“卖”作他人妇的村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又有谁愿意行此有违人伦之举呢?而且,由此得来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解除家庭的贫困,只能一次又一次陷入婚骗的困局。 据悉,发生在云南贫困山区的“婚骗”由来已久,当地政府部门并非全然不知,然而对此却一筹莫展。政府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真正理由可能是:他们无力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难以理直气壮地阻挡村民们的“生财之道”。 因此,我们不能用“贪婪”、“愚昧”、“可耻”等常见的道德词汇来评价“婚骗”中的人和事。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不能根除“婚骗”滋生的土壤,就没有理由去指责那些参与婚骗的“鸽子”和她们的家人。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云南媳妇”,还是受骗“买妻”者,他们无一例外都生存在我们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方。他们的“买”、“卖”行为,最初的原因都是两个字:贫穷。 贫穷不是罪恶,贫穷也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但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贫穷往往是滋生罪恶的土壤。“婚骗”这一畸形的“生财之道”,绝对不是靠一个杨洪的自首,靠几次警方的严打,靠当地政府的专项整顿就可以销声匿迹的,如果不能彻底铲除这颗毒菌滋生的温床,“婚骗”现象只会更隐蔽,危害性也更大。因此,作为政府一方,如何想方设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尽快让当地百姓走向富裕,远比解决“婚骗”这一具体问题更为重要。 麻栗坡县小弄乡一位参与“婚骗”的妇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之所以甘愿当“鸽子”,最初的理由是,她想到外面的世界、到大城市里走走看看,她不想再守着大山过苦日子了。因此,无论她的行为应该受到何种道德的谴责或是法律的制裁,这种朴实而良好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 来源:http://news.sina.com.cn/s/2006-07-12/10429441679s.shtml
上两条同类新闻:
梦想钓到“金龟婿” 不料被骗十余万女网友谋面险遭辱 无耻色狼获刑二年
|